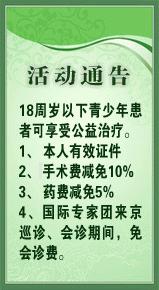您现在的位置: 首页 >> >> 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报
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报
作者:佚名 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21-11-24
 添加到百度搜藏 添加到百度搜藏 |
关键词: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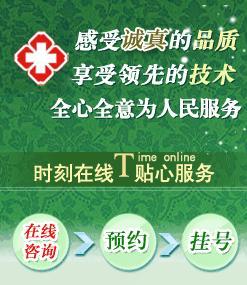
记者/韩谦实习记者/龙天音
编辑/刘汨
4月24日,刘强进行肺移植手术
普通肺移植患者的术后护理像是在“走独木桥”,对于新冠肺炎移植患者来说,这个过程和“走钢丝”一样凶险。
7月底,65岁的崔志强和54岁的医院和普通病房,相比其他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,他们走过了一段更长、更难的路,即使如插管、ECMO(人工肺)这样的手段都没能让他们脱离险境,直至遭遇病毒侵蚀的肺部被移植替换,两个人才从生死线上被拉了回来。
无论从医学还是人心的角度,这都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。
移植手术过后,崔志强又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90多天,一整层病房、20多人的团队,都只为他一个人服务。种种的不确定性让他的生命体征24小时处于监控之中,呼吸、血压、用药,以及排泄,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,在他身上都可能产生放大十倍的影响。
除了忍受疼痛外,病情如同过山车般的起伏也不断打击着他们的信心。刘强把这个过程比作不断循环地爬山,一开始拼命往上爬,好不容易快登顶了,“啪,一下子又掉下来了。”他一度想过咬舌结束生命,“那时候我已经挂在悬崖边上了,稍微松懈一些,就会掉下去”。
直到熬过了最难的时候,如今刘强一顿早饭可以吃下一个鸡蛋、喝掉一碗米粥,再回忆起医生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肺移植手术的情景,他才笑着说:“幸好当时点了头。”
7月29日,医院普通移植病房
“没什么可犹豫的了”
7月21日下午,在接受肺移植手术92天后,65岁的崔志强离医院(以下简称“医院”),医院继续治疗。第二天,经过医生许可,他如愿见到了5岁的外孙,半年来,女儿崔瑛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的笑容。
父亲转院后的第12天,崔瑛才给他办完全部出院手续——那是一摞叠起来足有1米高的结账单,医院三台打印机,全部费用累计多万元都由国家负担。
3个多月前,崔瑛不敢确定,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父亲。2月6日,崔志强因发烧被接到定点酒店隔离,次日医院就诊,9天后,崔志强的病情急转直下,呼吸困难,崔瑛与他失去了联系。
从护士每隔三五日在凌晨1点多发来的短信里,崔瑛了解到,父亲先是上了有创呼吸机,然后又换ECMO支持。她再多问下去,收到的回复总是相差无几,“大概意思就是还在维持治疗,但活下来的希望很小”。
那时候,电话响起时是一家人最紧张的时刻。崔瑛接电话时,母亲会离开几米远观察她的神色,“如果我脸色凝固些,她就不敢过来,如果我特别高兴,她就又跑过来站在我旁边听”。武汉封城的日子里,崔瑛最担心的是自己连送父亲一程的机会都没有。
4月18日,电话还是来了,医院告诉崔瑛,她的父亲有机会接受肺移植手术。“成功率并不确定,但不做是百分之百没有希望。”崔瑛觉得,自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。
在此之前,医院胸外科主任林慧庆已经完成对崔志强的情况评估。自3月7日以来,崔志强的的7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,算是一位“新冠后遗症”患者。呼吸机上显示的肺部顺应性指标为12厘米水柱,差不多是正常人指标的三分之一,肺活量的数据则降到了毫升,这意味着,崔志强的肺在休息了近60天后仍无法自我修复,不可逆的纤维化使它完全丧失弹性,不能再像吹气球那样完成回缩、舒张运动。如果不进行肺移植手术,持续的炎症将不断侵蚀崔志强,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,等待他的只有死亡。
除了肺以外,崔志强心肝肾功能正常、凝血功能基本正常、细菌感染得到控制,作为对患者有“高选择性”的肺移植手术,崔志强符合了严苛的手术标准,在他清醒的时候,也表达了同意尝试移植的意愿。
几乎同一时间,医院两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也接受了肺移植专家组成员的问询。在停掉镇静剂后,54岁的刘强点了点头,另一位73岁的患者则拒绝进行手术。
刘强于1月底在同朋友的聚餐中感染新冠肺炎,因病情迅速恶化于2月11日接受ECMO治疗,先医院、医院和医院。最终,刘强作为全世界有记录使用ECMO术前辅助时间最长的新冠肺炎核酸转阴患者,在他插管的第73天,也等来了匹配的供肺。
崔志强的手术在4月20日下午进行。前一天晚上,林慧庆失眠了。担心和兴奋围绕着她。在此之前,国内虽已进行了5例手术,但仍有些尚无法回答的疑问:万一患者手术后复阳,那么手术的意义在哪里?患者手术后远期存活状态如何?如果有医护人员感染怎么办?国际上可参考的文献只有4篇,还包括一个失败案例,一切都是未知数。即将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也令她兴奋,“医学的进步,就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尝试性工作。这中间会遇到波折,但我们会尽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”。
手术由林慧庆和肺移植专家组组长陈静瑜主刀。一个横贯胸腔约30厘米长的切口被剖开,胸骨被完全暴露出来。崔志强的肺是暗红色的,萎缩至正常状态下的2/3。新冠病毒的侵袭带来肺部不可逆的纤维化使它摸上去疙疙瘩瘩的。病肺被切除,来自于一位29岁脑死亡病人的肺被移植到崔志强身上,新鲜的肺呈淡粉色,跟海绵一样,摸上去很轻。
穿戴着5斤重的正压头套、四层手术服和三层手套,三级防护的措施为手术增加了许多难度。八个小时的手术后,兴奋劲已经过去,一种疲惫感笼罩了林慧庆,“就是那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”。
崔志强第一次进行坐姿训练
并发症来了
接力棒被传递到了术后护理组,对肺移植病人来说,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肺作为人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,更容易与细菌接触,移植肺又处于失神经控制状态,无法通过咳嗽、排痰等方式减轻炎症反应,导致肺部感染的几率增高。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由于此前长期卧床,身体机能处于很差的状态,更增加了康复中的不确定性。
医院从重症医学科、呼吸科、胸外科等科室抽调来6名医生、13名护士、2名康复师和1名心理医生,20余人的团队只负责崔志强一个病人,重症临时病区一整层楼成了他的专属病房。
在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光看来,普通肺移植患者术后护理过程像是在“走独木桥”,对新冠肺炎移植患者来说,这个过程则可以比作是在“走钢丝”,稍不留神,便会失去平衡。
第一个难关很快就来了。
4月21日凌晨1时许,做完手术的崔志强被推回重症监护室。观察一两个小时后,崔志强的高压降至六七十,两侧安置的胸管不停地排出血液,一晚上出血量达到多毫升。这意味着创面存在大面积出血,如果内部血凝块不及时清除,这里将成为细菌繁殖的“沃土”。
那个晚上,崔志强输了20多袋、近万毫升血。李光和7名医生、4名护士一直守着,到早上6点,尝试过各种方式止血无效后,肺移植专家组决定重新打开创面,进行开胸清创手术,寻找可能的出血点。
两个小时后,崔志强被重新推入手术室,林慧庆同陈静瑜再次站上手术台,对弥漫性的创面渗血使用氩气刀喷出氩气保护气,火焰烧灼渗血处止血,并对可能的出血点进行缝合、结扎。下午1点,手术结束,担心崔志强又出现渗血问题,在手术室继续观察24小时后,他才被推回重症监护室。
连串的措施在第二天开始见效,医生们逐步降低ECMO的氧气支持力度,在测试三个多小时后,崔志强的血氧饱和度等一系列指标维持正常水平。晚上8点多,崔志强完成ECMO脱机,这意味着移植肺开始发挥功能,可以自主呼吸了。在医院待了3天后,李光终于可以回隔离酒店洗上一个澡了。
“整个脑子都是麻的”,李光如此形容那时候的自己。崔志强在术后遇到的麻烦是此前未曾预料到的,术前,崔志强凝血功能的数据只比正常人稍差了一些,这对普通病人来说或许问题不大,但对新冠病人来说,术前的小问题都会在术后变成一个巨大的麻烦。李光事后总结,这或许与崔志强此前长期使用抗凝药物有关——为防止血液在接触ECMO管道表面时凝固形成血栓,需使用抗凝剂以抑制人体自身的凝血功能。
术后出血的问题困扰了刘强的护理团队更长时间,在完成肺移植手术24小时后,刘强也因出血过量进行了一次开胸清创手术,在尝试一次脱机失败后,直至5月6日,肺移植手术结束后第12天,刘强才完成ECMO拔管手术。
紧接着,肾功能损伤、细菌感染、抗排斥反应、胃肠功能等并发症陆续袭来。“一般病人有两三个并发症就已经很难处理了,没想到刘强全中了”,治疗中一连串的“意想不到”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史嘉玮觉得,自己“不像个经验老道的医生,倒像是个研读论文的学生了”。
有时候,刘强的治疗方案也无法完全依据既有经验操作——药物极少发生的副作用在刘强身上发生,一些治疗方案在刘强身上失去了效果。为了摸索出平衡各类并发症的治疗方案,史嘉玮需要盯紧刘强的每一个指标的细微变化。
挂在悬崖边上
刘强开始恢复意识的时候,身上插着17根管子。
手术前卧床余天,肌力为零级,意味着四肢完全瘫痪,无法完成肌肉收缩运动。简单的呼吸、吞咽、抬手等动作都需要进行康复训练。
长期卧床使他丧失了时间观念,他对疼痛最早的印象是在一天早上,刚睁开眼,护士们在为他清理身体,由于仍插着有创呼吸机无法说话,他吃力地伸手向他们比出了一个暂停的手势。那时候,他总会在晚上做各种奇怪的噩梦,有家人出意外的,也有自己被怪兽追着跑的,被惊醒之后,“那种疼痛感没法用语言来描述,全身上下哪哪都难受,好像把几辈子的病全得了一遍”。
“疼!”5月16日,医护人员为崔志强翻身时压到了他臀部的褥疮,由于长期卧床,崔志强腰骶部长出了一块7x13厘米的褥疮,表层的皮肉全部腐烂,骶尾骨裸露可见。
崔志强因疼痛发出的强烈的气流冲破了气管切口上的气囊,经由声带发声,这是崔志强术后第一次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。“那会儿还只是在练习呼吸功能,还没有用上语音阀,他这一声,肯定是用了很大的劲”,当时在场的康复师马思亮回忆。
除忍受疼痛外,病情如同过山车般的起伏也不断打击着他们的信心。刘强把这个过程比作不断循环地爬山,“一开始拼命往上爬,好不容易快登顶,‘啪’,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你再努力往上爬,又狠狠地摔下来”,反复几次后,刘强开始对自己是否能够康复产生怀疑,他甚至考虑好了用咬舌的方式结束生命,“那时候我已经挂在悬崖边上了,稍微松懈一些,就会掉下去”。
六月中旬,可以逐步练习行走的刘强出现严重的排斥反应,氧合指数下降,呼吸又变得困难起来,全身也如同连锁反应般开始疼痛。抗排斥药物量的增加,又使得身体免疫力降低,紧接着细菌感染又来了,史嘉玮回忆,“胸片拍出来两个肺都是白的,发生了很严重的炎症反应”。
那时候,刘强在凌晨给护士长杨林杰发去
| Tags: |
| 查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医院 |
| 查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治疗 |
| 查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医生 |
| 查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专家 |
| 查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方法 |
|
|
以上文章“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新冠肺移植患者深度报”信息只作参考,诊疗要到正规医院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,任何疾病都要做到早发现、早治疗、早预防,严重者务必到专业的硬皮病医院治疗。
热点关键词
-
尚无数据
-
尚无数据